文史选粹
什么是好的大学生活?
周保松认为,一所真正伟大的大学,不在于高楼,不在于大师,而在于学生,在于是否有能力培养出具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的知识人
什么是好的大学生活?在相对主义成为绝对律令的年代,回答这个问题是困难的。但是,何兆武先生的《上学记》、齐邦媛先生的《巨流河》在读者之中口耳相传,又说明人们对于“好的大学生活”有着相似的期待。答案并不复杂,无非是在大学可以充分享有精神生活和公共生活:精神生活重在思想层面,重在个体独立;公共生活重在实践层面,重在公民参与——两者互有关联,各有侧重。
何兆武和齐邦媛两位先生的回忆过于遥远,总让人生发“恨不相逢”的感慨。仅仅这样感慨,“好的大学生活”不会从天而降。周保松的《走进生命的学问》展现了一种可能,在今天,“好的大学生活”并非传说,不仅是可欲的,也是可能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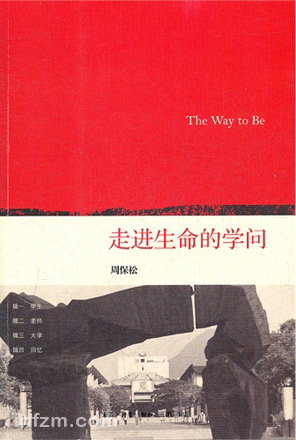
《走进生命的学问》 周保松 著 北京三联
周保松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,后来于伦敦政经学院留学,毕业后回母校执教。这本书讲述了他的大学生活,曾经的学生时代和现在的教员时代。周保松对大学精神有着深入思考,承认个人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,但反对以价值中立为由拒绝价值判断。他以香港中文大学为例,指出中大精神是“价值关怀和社会批判”。这不仅适用香港中大,也适用于任何一所愿意把自己定位于大学而非职业培训学校的大学。
这几年,内地部分优秀考生转投香港高校,已成风气。香港的大学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,自不待言。但作为香港中文大学教师,周保松没有美化香港的大学教育。在香港中大40年校庆之际,周保松撰写了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,历数香港中大校友对母校的批评。如果仅从这些批评来看,香港中大似乎还不如内地一所专科学校在校庆时获得的称许。但是,周保松接着指出:“这种深刻的自我反省恰恰是一所大学最为需要的。”
周保松对于大学体制有着直接的批评,不仅批评大学有成为职业培训学校的趋势,还指出大学存在一个严重却常被忽略的问题,即重研究、轻教学。大学是学术研究机构,与其他研究机构又有着根本不同,不仅要承担研究,还要承担教学。但是,研究可以被量化、评估和排名,教学却很难如此表格化,所以对教师的评价几乎以研究为主。周保松感慨,在这种大学体制之下,“用心教学,等于和自己过不去。这种将老师从学生身边赶走的制度若不改变,价值教育将无从谈起。”
对大学体制的批评并不鲜见,在媒体上甚至经常可以读到大学校长开会“炮轰”教育制度的新闻。有时,“炮轰”不是为了纠正,而是为了说明自己“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”,只能顺应时势。周保松对大学体制的批评,更多的是一种自我反省,通过反省而行动,把绝大部分时间用在与学生的交流上,改变这种惯性。他认为,“一所真正伟大的大学,不在于高楼,不在于大师,而在于学生,在于是否有能力培养出具独立精神和自由意识的知识人。”
在周保松看来,大学的理念主要是回答两个根本问题:一个是“我该如何活”,一个是“我们该如何活在一起”。这与“价值关怀和社会批判”有对应之处,也与周保松关注的人生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有关,一个关于精神生活,一个关于公共生活。
大学时代,20岁上下,正是对人生产生困惑的时期。在信仰缺失的情况下,意义危机尤其严重。有的地方习惯用灌输式的思想教育解决意义危机,但是收效甚微。在迷惘之中,人们很容易走向两种归宿:工具理性和心灵鸡汤。在工具理性的指挥下,大学成了职业培训学校,学生的终极目标是谋职,以至于卧佛寺成为毕业生喜欢的去处,原因是卧佛寺和offers谐音。信仰也被工具化了,这与其说是“工具理性”,不如说是“工具非理性”。与此同时,人生哲学被等同于心灵鸡汤,融励志和抒情于一体,开放、包容和多样性被理解为“怎么样都行”,最后得出一个价值虚无的结论“只要活着就好”。也有不满足于工具理性和心灵鸡汤的大学生,以存在主义的方式面对虚无。
“未经省察的人生,是不值得过的。”苏格拉底的这个说法,意在表明人生的意义蕴于自我省察的过程之中。这主要有两重含义:一、重在“自我省察”,没有强迫他人必须省察的意思,否则变成了思想改造;二、省察的价值在于过程,而非结果,不需要一个标准答案。
大一的时候,周保松选修了陈特先生开设的课程“哲学概论”。陈特曾先后就读于香港珠海书院和新亚研究所,师从钱穆、唐君毅、牟宗三等先生。在第一节课上,陈特讲解了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,让周保松感受到哲学的魅力,后来决心“弃明投暗”,从工商管理专业转至哲学系。陈特先生晚年罹患重病,周保松和朋友经常前去探望,讨论死亡、意义、善恶等问题。书中收入了他们的对话,很少有探望病人时常见的那种无力的安慰性的言辞,关于人生诸种问题的对话本身就是在赋予人生以意义。
在追忆另一位老师沈宣仁先生时,周保松曾问沈先生什么是美好的人生,沈先生用麦金泰尔的话回答:“一个美好的人生,是一生不懈地追求美好人生的人生。”这句似乎同义反复的话,重申了“过程”的意义。只问胜负不问是非,只重结果不重过程,为了目的不择手段,恰恰是价值虚无的源头。
精神生活从沉思开始,但不能止步于此,需要在交流中显现,“我该如何活”与“我们该如何活在一起”不可分离。这不是在召唤那种旨在消融个体的集体生活,而是试图构建一种个体能够更好实现自身价值的公共生活,不是由一个个只会服从的奴隶组成丛林社会,而是由一个个独立的自由人组成公民社会。“我与社会的关系,其实是‘我’与‘我’的关系。”陈特先生如是说。
除了陈特先生的“哲学概论”,在范克廉楼的经历也对大学时代的周保松影响深远。香港中大学生活动中心位于范克廉楼,最重要的是,香港中大学生会的核心——干事会和学生报编辑,由全校学生票选,经费来自学生。周保松虽然转入哲学系,但是大部分时间用于各种公共活动,通宵达旦地编辑《中大学生报》,策划近千同学参与的大规模论坛,不仅关注大学的问题,也关注香港的事务。
担任教师之后,周保松更是致力于开拓公共生活的空间。他每开一个新班,都会开设电邮讨论组,与同学交流,两年时间就有数十万言,整理编辑成《政治哲学对话录》。翻开《走进生命的学问》,开篇就是他写给学生的公开信,其中《独一无二的松子》已经广为流传。他发起犁典读书组,与学生一起阅读哲学原典,一起郊游,一起去大排档宵夜。他会邀请学者举办讲座,有时在演讲厅,有时在露天广场,有时在自己宿舍的客厅。周保松和他的学生们,参与讨论各种香港的公共问题,在香港的公民行动中发出重要的声音。通过这些实践,周保松将学问和生命(不仅是生活)融为一体。治学本来就应该和问道有关,此所谓“学问”,只是治学慢慢地变成一门技术,成为了“学术”。
阅读《走进生命的学问》,就像在和周保松对话,许多细微之处悠然心会。只是在对于一些问题根源的看法上,我和他稍有分歧。由于语境不同,周保松反对“小政府,大市场”的格局,对市场、经济、商业多有批评,认为它们的逻辑过于强势,应当加以抵制;我却倾向于认为市场、经济和商业有促成开放理念和契约意识的可能,它们的问题主要是因为权力过多介入,无法独立和竞争,以至于出现“大政府,小市场”的现象。除了语境的不同,在理论资源上,周保松受罗尔斯影响很大,而我更接受诺齐克的说法。两者虽有冲突,并非水火不容。周保松曾写过纪念诺齐克的文章,我对罗尔斯也怀有敬意。
关于“什么是好的大学生活”乃至“什么是好的生活”,我们没有分歧。如果思想完全一致,是最没趣的;如果思想完全不同,对话会很困难;具有基本的共识,同时又有差异,这是进行思想交流的理想状态,也是生活的美好所在。




